本篇文章3192字,读完约8分钟
高校“挖人战”下的“职业跳槽教授”
“大学老师换工作。这有点像有些人离婚。他们离开得越多,珍惜得越少,感情越少。”一位西方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不情愿地将他周围一些大学教师频繁跳槽的情况进行了比较。

几千公里之外,中国东北一所大学的长江学者张龙(化名)正在表演“离婚和再婚秀”。每隔三至五年,他就换一所大学,最后一次换工作时,学校付给他6000万元的科研经费,前雇主投入的2000万元科研经费被闲置,围绕他组建的科研团队被迫解散。

这位教授40多岁时被评为长江学者,现在已经是第三次跳槽了。
毫无疑问,大学之间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动可以促进人才的成长,优化智力资源的组合,充分发挥其作用。然而,与此同时,一些高校人才的非正常流动导致了一场“挖人之战”,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像张龙这样的“跳槽教授”是高校“挖人战争”负面影响的缩影。

有三个蜻蜓和狡猾的兔子的洞穴
“职业跳槽教授”为了利润而跳槽,寻找官员
“这样的人是钻空儿子的系统,让国家资源流入他们的口袋。”东北某985大学人事处处长告诉记者,“职业跳槽教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蜻蜓点水”型和“狡猾的兔子三洞”型。

拿一点水来说:一个就业期被换到另一个单位,每个学校呆三到五年。“只要雇佣期一结束,它就会值很多钱。如果学校不给钱,它就会跳开。如果你想说他违法了,他在法律上是清白的。但你不得不说他没有造成伤害,这怎么可能呢?”湖南一所地方高校的人事部主任向记者承认,“蜻蜓点水”教授是最麻烦的。这类教授往往资历深厚,学术水平高,社会关系广泛。当五年雇佣期到期,合同续签时,他们将提供高价条件。如果他们不满意,他们会换工作。

“这些人很聪明。他们可以通过跳到一个单元,进行项目和写论文来快速适应。然而,我们发现他们的科研成果往往是重复和短期的,他们的简历也很漂亮。学校的学科建设和人才梯队培养似乎与此无关。”上述人事部门的负责人表示,学校现在已经“胆战心惊”,甚至不敢对某个老师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投资。"如果钱减少了,当预约期结束后我该怎么办?"

兼职雇主多,科研成果少。王晓(化名),一位来自大学的年轻学者,成功申请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项目,并成为项目主持人。作为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的主持人,他曾在几所普通高校任教。“先去一个地方,领一笔房款,买一栋房子,然后再去另一所学校。”

王晓原大学人事处主任说,学校收到了一封来自一所省立大学的信,信中对老师的行为提出了质疑,“但那时候,我们学校已经没有人了。”为了引进人才,其他大学的很多人事程序都不规范,最后只能吃个亏。即使是分配给他的房子,产权也已经被拿走了,至多几年后还会再拍一次。”

许多受访者表示,一些大学教师在多个单位任职或兼职,那些拥有光鲜头衔的人被“多名员工雇佣”,他们从各方获得了巨额投资,也有很多兼职工作,但他们的科研成果却少得可怜。

一位接受采访的专家告诉记者,无论是"蜻蜓点水"还是"狡猾的兔子洞",都有两个目的:谋利和求官。“我从40岁开始跳,65岁退休,我被聘用了5年。我至少能跳三四圈。每一轮都有家庭津贴,我可以赚很多倍。”也有一些人在原来的下属院校里无法得到一个正式的职位。在两三年时间里,他们跳槽到省属高校担任部门副主任,很快又跳槽到市级高校担任部门主管。

“金帽子”思想的危害
一些地方高校已经成为“几次跳跃”的重灾区
“今年,有200多个度点开始评估。因此,各大大学都开始“挖人”,许多“跳槽”的教授都渴望跳槽。”一些接受采访的高校人事工作者坦言,每当涉及高层次教师数量的评估开始时,许多高校都会进入“人才动荡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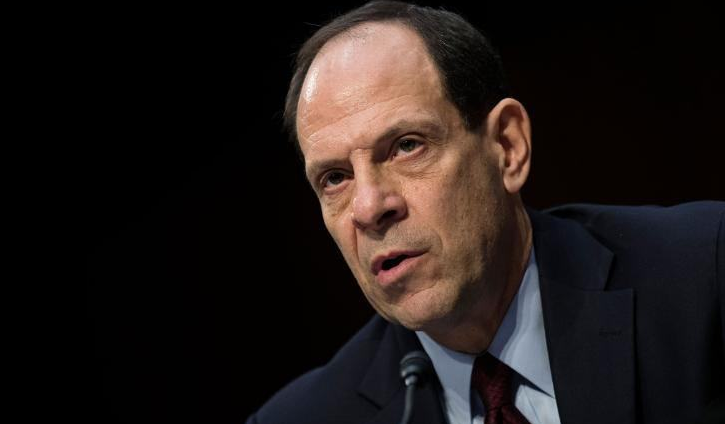
“我们有一个学院院长,他是一个年轻的长江学者,年薪大约40万。两天前,广东的一所学校开出了130万英镑的年薪来挖他。因为博士项目要被评论了,我想挖一顶‘金帽子’来增加我的筹码。”一所985大学的人事部主任说。

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褚赵辉告诉记者,“跳槽”教授的出现有一个背景,那就是在学校里“挖人”是一种短视行为。“介绍就可以了。至于他将来会为学校发挥什么作用,目前还没有考虑,主要是满足人才评价指标。”

与名牌大学相比,一些普通高校更受“金帽子”思想的影响。
华中地区一所普通高校的人事干部告诉记者,省属高校的经费主要来自省级财政拨款,与部属高校相比“少才少钱”。在此背景下,教授拥有“长江学者、全国杰出青年学者、千人计划专家”等称号。,可能会给学校中的某个学科带来质的变化。

“我们不是从9到10,而是从0到1。所以我们特别愿意付出很多代价。然而,当我们把有限的资金集中在一两个人才身上时,带回来的人却是跳槽,这将对整个教学团队的心态产生很大的影响。”人事干部很担心。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必要。记者了解到,西部一些省属高校在人才数量评价指标的压力下,一方面不能花大量的钱来改善教师待遇,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花有限的钱来吸引顶尖人才来“砸指标”,这导致教师薪酬平衡严重倾斜,影响了教师的心态。

一所大学的人事部主任将这种情况比作“等待红灯”:“每个人都在过马路,一群人都在真诚地等待红灯。”突然,一个人从天而降,他在马路对面被杀,没有人抓住他。其他等待红灯的人会迫不及待地想走,觉得等待是不公平的。这损害了整个人才市场的公平性。”

最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地方高校在遭遇“几次跳级”后,无法挽回损失。“即使有些人在合同还没有到期的时候换了工作,补偿和返还部分有时也会被延迟,而且会丢失。真是浪费资源!”

受访的高校人事工作者透露,面对不合理的“挖人战”,他们基本上受道德层面的契约精神约束,真正诉诸法律的人很少。"这是最后的手段,基本上不会使用它."

“跳槽病”的多管齐下管理
完善机制,搭建平台,调整接力棒
接受采访的专家、高校管理者和一线教师认为,“跳槽教授”的出现是高校人才机制不完善、教师信息平台建设不完善、考核政策调整的标志。要治疗“跳槽病”,必须多管齐下开药

首先,一些“人才工程”应该增加空的限额,以避免“跳槽镀金”的现象。接受采访的大学管理人员承认,像长江学者这样的人才项目倾向于西方。一些“跳槽”的教授钻了孔子体系的空子,给它镀金。在激烈的东方竞争中很难获得冠军,所以他们跳到西方去参加评审,然后“回国”。

“你能在人才项目上限制空吗?例如,如果长江学者是因为从东到西的区域照顾政策而被选中的,他们应该采取单独的序列,如果他们跳回到东,他们应该被重新评估。享受过地区医疗服务的学者如果换工作的话,应该会受到空的限制。”采访大学人事主管建议。

其次,为高校教师搭建一个信息共享平台,让专业诚信可以追溯。“在我们学校引进人才时,有两种人是坚决不引进的。首先,看看过去的简历。如果你换了两次以上的工作,不要。第二是看兼职工作的数量,太多的兼职工作,不要。”一所985大学的人事部主任透露。

然而,实施这些标准仍然很困难。“现在哪个老师在哪个学校都有职位,我们都是‘黑眼睛’,没有信息共享的平台,我们只能靠自己查百度。”接受采访的专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建立高校人才交流的信息共享平台,可以查询人才的简历和兼职情况。这样,雇主可以评估和预测人才的职业操守,同时也迫使人才约束自己。

第三,调整考核指挥棒,避免“金帽子”催生人才异化流动。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张少雄认为,像“跳槽教授”这样的人才的异化和流动,根源在于评估指挥棒下的投机。“一些院校希望找到一个‘唯利是图式’的科研团队。第一,“金帽子”有更多的好指标,第二,论文和项目有更多的好结果。众所周知,纪律能力和学校建设是慢慢沉淀出来的,不可能又快又快。”

受访的高校管理者呼吁弱化对某些人才的量化指标要求,更加注重学校和学科的分配机制和考核指标的长期积累。“强大并不强大,你不能只看有多少‘金帽子’,否则,‘职业跳槽教授’的野火永远不会把他们完全吞噬。”(记者袁玉婷、严瑞)
标题:高校“挖人大战”:现谋官谋房的“职业跳槽教授”
地址:http://www.aqh3.com/adeyw/8111.html

